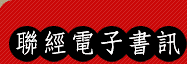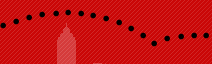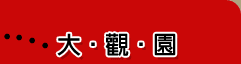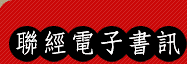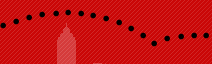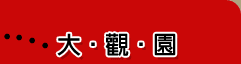根著我城: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
作者:陳智德(CHAN Chi Tak)
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,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,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「古文獻資料庫研究計劃」助理編輯、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站計劃」副研究員等職,現任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。研究領域包括香港文學、中國新詩、中國現代文學,亦從事文學創作,2012年獲選為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「國際寫作計劃」之香港作家,2009年起參與陳國球教授主持之「香港文學大系編纂計劃」,擔任副總主編,2015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「香港藝術發展獎:年度藝術家獎(藝術評論)」。著作有《板蕩時代的抒情: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》、《地文誌: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》、《這時代的文學》、《愔齋讀書錄》、《抗世詩話》、《解體我城:香港文學1950-2005》,另編有《香港文學大系1950-1969•新詩卷》、《香港文學大系1919-1949•文學史料卷》、《香港文學大系1950-1969•新詩卷一》、《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•葉靈鳳卷》、《三四○年代香港新詩論集》等。
※ ※ ※
了解香港文學,必須從這本開始!
香港文學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對於「非本土」的否定之上,也不是簡單地由無到有的過程,實際上存在更多的矛盾、游離。本土與非本土共同構成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複雜性,結合流動與根著的辯證,作為本書《根著我城: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》回顧、論述戰後至2000年代香港文學的核心。
※ ※ ※
第十三章/本土的自創與解體──從《我城》到《白髮阿娥及其他》
引言
香港作家,特別具本土成長經驗者,如舒巷城、侶倫,或戰後在香港成長一代作家,如西西、也斯、鄧阿藍、鍾玲玲、辛其氏、李碧華等作家筆下的香港,往往因其本土認同而有別於南來作家對香港的疏離,該認同不是一種地方主義,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並非簡單的認同或身份上的分類,在認同以外,許多作家都意識到本土認同與粉飾現實、自我膨脹的分野。
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能具自我反思的關鍵,在於它不是由官方推動,而是一種民間自發的思考,形式上有時採用自創的新形式,有時借用既有的民間傳統,以至改換既有的非本土觀念。在西西寫於七○年代的小說《我城》,尤其見到這種本土的自發和自創,是如何透過新建的觀念,以至借用、改換既有的殖民地觀念而成為民間自身的認同觀念,在這一點上,《我城》具重要的開創性意義。
二○○五年,西西獲得第三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,然而在許多讀者心中,早已頒予西西更難得到的榮耀,因為她的小說總是以不同形式,為讀者帶來真正的感悟、以至看穿世事的假象。她的文學生命,由五○年代的香港開始,一直試驗、引進不同的現代小說技巧,六、七○年代是她在香港報紙以專欄方式逐日發表作品的高峰時期,同時亦參與編輯、創辦文學刊物,六○年代曾擔任《中國學生周報》「詩之頁」的編輯,一九八○年參與創辦《素葉文學》。八○年代,西西以小說〈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〉而廣受臺灣文壇注目,繼而由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陸續出版多種小說集,更先後編成《紅高粱》、《閣樓》等四冊小說選集,向臺灣讀者介紹八○年代中國大陸「新時期」小說家;九○年代經歷疾病纏繞,仍寫出《哀悼乳房》、《飛氈》等長篇,西西以她的開創性、生命力、文學識見和持續的墾殖,超越了一切獎項和名譽的得失。
二○○六年出版的小說集《白髮阿娥及其他》有描述西西本人對疾病的反思,更多篇幅談及回歸以後至二○○○年代,香港社會在「全球化」經濟中的轉變,小說中的香港環境,以及西西的筆調、對香港本土的觀念,與七○年代的《我城》有很明顯的差異。
《我城》一九七五年於《快報》連載,一九七九年出版單行本,九○年代多次再版,不少論者撰文評論,可說是香港文學的經典名篇,它的重要性在其鮮活創新的語言,也在其本土性,以七○年代青年的角度,從身份認同的割裂和殖民符號的虛無中,重新轉化出一代人的本土認同,當中的過程值得深思。《我城》以年輕一代的生活反思本土身份和認同的可能,小說中的角色阿果、阿髮和悠悠等人不單經歷共時的現在,也沉思和追溯城市的消逝事物和觀念,以他們對新事物的「零度經驗」,為一個逐漸成形的「有機社群」造象。
二○○六年的小說集《白髮阿娥及其他》,包括寫於二○○○至二○○一年的〈解體〉、〈鷲或羔羊〉、〈照相館〉、〈巴士〉、〈共時〉等篇,都以中年人的角度,重思本土經驗的變化,當中最重要的表徵,是「有機社群」的解體。王斑以中國內地和臺灣的小說作品如王安憶的《長恨歌》、《紀實與虛構》和朱天文的《世紀末的華麗》、《荒人手記》等小說作為例子,提出文學如何揭示全球化導致「有機社群」解體,將記憶的氛圍去魅,也許正有助於我們思考,從七○年代的《我城》到二○○○年代的《白髮阿娥及其他》,其間本土性思考轉變和差異的本質。本文嘗試透過對《我城》與《白髮阿娥及其他》二書的分析,探討西西如何在七○年代透過新建的觀念,以至借用、改換既有的殖民地觀念去建構本土意識,轉化出本土認同,而二○○○年代的《白髮阿娥及其他》又對這認同提出怎樣的質疑,由此思考香港文學中的本土價值的不同層面。
一、認清了「無」之後,重新建立的「有」
西西早年以藍子、張愛倫等筆名在五○年代香港的《人人文學》、《星島日報•學生園地》、《詩朵》和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等刊物上發表詩和小說,一九六六年出版第一部中篇小說集《東城故事》,六○年代中期主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「詩之頁」,七○年代參與《大拇指周報》的編務,七九年與友人創辦素葉出版社,出版「素葉文學叢書」,翌年再出版《素葉文學》雜誌。八○年代初,她在香港已出版了詩集《石磬》以及《東城故事》、《我城》、《交河》、《春望》、《哨鹿》等五本小說集,自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一書後,作品多由臺灣出版,六○年代的《東城故事》後來亦由臺北洪範收進《象是笨蛋》一書再版。
六○年代西西的小說,一方面頗見電影敘述手法的轉化,這時期西西也實際上從事過電影編劇工作,參與拍攝青年實驗電影和撰寫影評。觀乎〈東城故事〉,篇中不時插入電影分鏡劇本的指示,尤見電影敘述手法的影響;另一方面,六○年代在港臺兩地青年間也是存在主義思潮盛行的年代,〈東城故事〉中虛無和灰暗的調子其實也是當時的時代氣氛,不過西西的處理在語言上仍見指向性,並不完全虛無。小說透過當時年輕一輩受卡繆和卡夫卡影響至幾近氾濫的語言裡,反覆質疑現實世界的真實性;敘事者提出一個一個存在主義式的設問,看似虛無和個人化,實質指向「香港是一個怎樣的世界」這樣的思考,背後是一種不相信或不滿於既定說法的態度,把六○年代的虛無引向新觀念的探尋和反思。
七○年代的西西擺脫存在主義時期,其中最重要的作品無疑是《我城》。西西曾說《我城》是要用活潑的語言,寫給七○年代香港的年輕一代。除此以外,《我城》在書寫城市經驗及回應七○年代「本土化」問題上,有更重要的意義。
西西的《我城》本以專欄形式,以「阿果」為筆名發表,一九七五年間逐日連載於劉以鬯主編的《快報》副刊,七九年由素葉出版社首次出版單行本。《我城》提及不少七○年代的時事,如保釣示威、能源危機和夏令時間,寫年輕一代的生活和「他們的城」,但不直接「反映現實」地寫,也不賣弄特定歷史事件和個人經驗,如果說《我城》表現出一種本土精神,它的價值也在於處理本土題材的態度:本土並不等於加入本土地理名詞景觀,而是站在對等的角度,關注社區和民眾過去和今日的各種情況,也透過文學性的具有想像的語言,建立思考和批評的方法和空間,最終要建立的不是排外和自我膨脹,而是人文關懷。
《我城》整部小說寫城市,更寫觀看城市的方法,特別是年輕一代帶著文化醒覺的目光,拋卻既有的經驗、觀點和方法,如第十七節「字紙和尺」的故事中,字紙對讀者說:「請你不要拿那些尺來量我」,嘗試提出自己的獨立角度,為日常事物重新定義:「電梯是一種不必動用兩條腿攀樓梯的機器」,論者指出這是一種「零度經驗」的方式,所謂的「零度」並非指完全抹煞既有經驗,而是以「零度經驗」重新感受城市,在文本的空間內「去除習以為常的經驗障礙」,「以首次看見一九一件事物的態度去觀察它的外貌和理解它的特性」,「重新體驗現實世界」。「零度經驗」實際上也是一種重新命名世界、改寫現實既定觀念的方式,可追溯至西西寫於六○年代的《東城故事》,《我城》用年輕人的角度模擬七○年代現實中的新事物,近乎陌生化的手法指向對所見事物的重新思考,有如《東城故事》的語言,背後是一種不相信或不滿於既定說法的態度,指向對香港七○年代種種既定觀念的批評,正有感於舊有的語言和方法,如寫實主義反映現實的方式,無法有效表達複雜的現實,故另行建立新語言和新的觀察城市外在現實的方法。